[导读]《中央日报》副刊虽属国民党党报副刊,但并未完全成为宣传党义的传声筒。表现上看,这是因为执政党缺乏文艺和学术人才,不得不借助党外势力,根本上是其对知识分子和言论还是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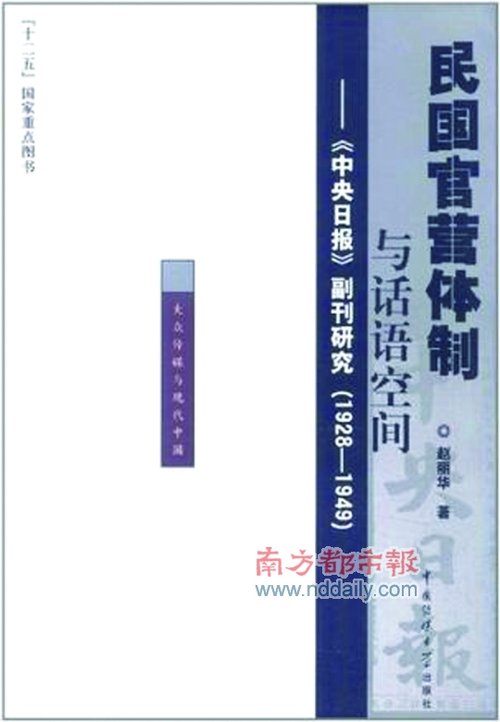
《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:〈中央日报〉副刊研究》,赵丽华著,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,32.00元。
在以往的报刊史研究中,《中央日报》并不为人重视。因为在一般的印象中,它是国民党的党报,负责宣传党纲党义,带有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。诚然,我们翻阅《中央日报》,发现其正刊部分的意识形态色彩,与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相比的确较重(也并未到离谱的程度),不过其副刊却未必如此。以1934年为例,周一至周日为社会调查、戏剧、农光、文学、科学、教育、医学周刊,编者分别为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言心哲,齐鲁大学戏剧学教授马彦祥,金陵大学农光社、储安平、孟广照,江苏镇江教育学会,南京丙寅医学社。每天出版的《中央公园》和《中央日报副刊》则由储安平总括其事。因此,完全以先入为主的“党化”二字将此报纸一笔抹杀,无疑是一种误解。
赵丽华的《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:中央日报副刊研究》,是国内第一本研究《中央日报》的著作。由于《中央日报》卷帙浩繁,副刊种类极多,该研究回避以往全景式线性梳理报刊发展史的方式,新辟路径,以“戏剧运动”、“民族话语”、“党外编者”、“国都书写”等四个专题,分门别类收集资料,研究副刊中的话语生态。相对于其他专题,最值得一谈的是“党外编者”部分。我们看到,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党报,大部分副刊编辑竟然是党外编者。这些党外编者在大方面认同于现行政治体制,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,并不负有直接宣传党义的责任。《中央日报》各个副刊在他们的主导下,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与正刊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。
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无疑是储安平和他编辑的三种副刊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,他的名字至少有七年和《中央日报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尤其在1933—1936三年的时间里,他担任了《中央公园》、《中央日报副刊》和《文学周刊》的编辑,可谓直接塑造了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的话语生态。从中可见,储安平以一种严肃、负责、公正的态度经营副刊,发表了大量文化批评、社会评论和文学方面的文章,发起过对诸多文化事件颇具声势的讨论。尽管他也刊发了不少批评鲁迅和左翼文学的文章,但这和他本人不认同左翼文学有关,而非迎合国民党的文艺策略。他尽可能将副刊打造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场地,在编读互动方面非常热烈,广泛吸纳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参与。即使限于党报性质,不能进行真正的政治批评,但还是做到了以建设性的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,成为当时国内报纸副刊的典范。
在副刊的党外编者群中,还有著名作家梁实秋,在《新月》时代,他曾是国民党的坚决反对者。在《中央日报》时期,他编辑《平明》副刊,宣传“抗战无关论”,否定被民族主义和左翼作家绑架的抗战文学;孙伏园则将副刊当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园地,在言论上对左右翼文人都予以一定的接纳。即使如党内编者王平陵,虽然肩负着捍卫三民主义文学的重任,却也表现出一种官方文人的探索气质,持一种软性的编辑策略。总之,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的编辑大多具有一定的独立权限,不同的人对副刊有着不同的影响,但基本都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各类言说复杂多样,话语之间多有张力,随处可见开放、丰富和多元的色彩。甚至,副刊言论有时展现出一种开阔博大、兼容并包的特色,如果忽略其报刊名头,很难将其与“党报”二字联系起来。
值得一提的是,《中央日报》在给编者以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之外,更多的是其在当时的知识、学术传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。不过,由于篇幅限制,以及讨论主题有限,作者在书中甚少提及这一方面。我们看到的是,《中央日报》的大多数副刊都以介绍新知和传播学术为主。比如前面提到的几种文学、科学和学术周刊,在《中央日报》中一直存在成为常态,而非昙花一现。除此之外,主事者还探索性地开辟了电影周刊、防疫周刊、市政周刊、建筑周刊、文史周刊、民风周刊、妇女周刊等板块,编辑者也多为北大、中大的教授们。许多周刊为同时代的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所无,而且质量并不次于上述两份报纸的副刊。其中介绍的现代科学、文学、农业知识,就深度和水平来看,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。由于其属中央党报,不刊载市井琐碎新闻,发行可达全国多数偏远地区,因此其对三四十年代中国民众的启蒙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其不注重批判,而注重一点一滴建设的理性态度,实际非常值得报刊研究者重新审视。
《中央日报》副刊虽属党报副刊,但并未完全成为宣传党义的传声筒。表现上看,这是因为执政党缺乏文艺和学术人才,不得不借助党外势力,根本上是其对知识分子和言论还是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。中央党报的副刊如此,其他非官方背景的报刊杂志更是自由言论的场地。正因为这样,才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舆论的黄金时代。这对知识分子来说,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运。不过,这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种“不幸”,正因为其缺乏“警惕性”,借助党外知识分子担任编辑,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文化策略,导致在其喉舌之内都没有真正建立起系统的意识形态文艺和文化。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,未必和文艺和文化上的“失败”没有关系。
韩戍,《南方都市报》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